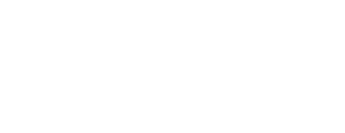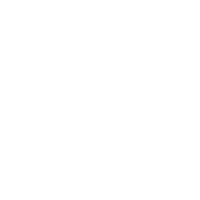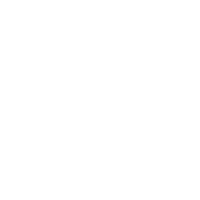丝绸之路上的美食与生命故事|三明治
春节期间我陪家人在阿联酋旅行,美食当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阿联酋作为国际移工大本营,汇集了各国美食。我也绞尽脑汁每天变着花样带家人品尝各地佳肴,争取好多天不重样。
我原认为能文思泉涌,轻松写出来好多美食鉴赏文,可是我却发现大部分餐厅虽有美味,但因为缺少情感上的联结,让我毫无写作的灵感与动力。比如本地中东餐厅,虽然用餐环境复刻了传统贝都因风格,手抓饭、红茶、烧烤等食物也都让我和家人们大快朵颐,但我对它们的感觉就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这一层“好吃”上。
而那些为数不多让我能有感而发的食物,似乎都是我在某时某地产生过一些联结的,而且大多来自全球南方地区。每一次品尝,特定的味道都能牵动我记忆中的某些故事和影像。不过,记忆是不断在积累的,现在也在转瞬间成为历史。跟着时间的流逝,很多食物与我的关系,会一步步加深。我就静静等待吧。
记得在印度工作的时候,街头巷尾的小卖部总是最热闹的。每次经过,总有好多男性悠闲地站着喝茶,一杯又一杯。有的拿着小纸杯,翘着兰花指,腆着圆鼓鼓的肚子,盯着路上的车水马龙。有的则激情输出,一只手挥舞着,摇头晃脑,颇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气势。有段时间,我也会带上管家一早煮好的Chai,装在大保温壶里,供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喝。印度的办公室文化和中国很不同,大家开会或闲谈的时间总能占个大半天,这些时候Chai便是必不可少的了。通常一大壶Chai,不到午餐时间就喝完了。
而在我目前居住的南亚移工密集的海湾城市里,虽没市井气息浓厚的街头小贩,但路边有很多南亚小吃门店,供应包括Chai在内的丰富多样的美食和饮品,物美价廉。小店里售卖的Chai通常是已经做好保存在保温壶里的,虽然香浓甜醇,但对我来说甜度偏高,于是我打算自己在家里做。
我在网上找到了很多Chai的配方,对比后选择了一位居住在英国的印裔博主分享的相对简单的食谱。她的分享中最打动我的一点是香料的运用无需固定,通过你自己的喜好添加即可。这让我放下了最初对制作所谓“地道的”Chai的执念,而可以更放松地从自己相对熟悉的配料开始入手。
分享一下我到目前屡试不爽的食谱:1杯水,1勺红茶粉,1杯牛奶,2小块生姜,1块肉桂,2-3颗丁香,2颗小豆蔻,3-4颗黑胡椒粒,1小块方糖。先将生姜、小豆蔻、丁香、黑胡椒粒捣碎,倒入煮开的水里,搅拌后再加入红茶粉,煮2分钟。再往锅里加入糖和牛奶,小火慢煮2分钟(注意控制火候并多多搅拌,别让奶溢出锅)。此时Chai已经做好,在杯子口架个过滤网,倒出来的时候将渣滤掉,就可以享用一杯热腾香浓的Chai啦。
自从学会自制Chai之后,我每天上午必喝一杯。捧起热乎乎的杯子,迫不及待地呼呼喝上两大口,浑身上下涌过阵阵暖流,头脑也顿时清醒起来,连咖啡都无痛地戒掉了。经期时我则会将方糖改成黑糖或红糖,个人感觉有缓解痛经的效果。
Chai在稍稍冷却后,表面会结一层焦糖色的奶皮,用嘴轻轻一吹,会俏皮地褶皱起来。有的印度朋友会用指尖快速地拎起这层奶皮塞进嘴里,我第一次见时颇有些震惊。朋友回味着奶皮的美味,意犹未尽地对我说,“我奶奶说呀,这层奶皮是最有营养的。”
野猪是村民带着家里的狗狗一起猎到的,特别鲜香美味。肉质紧实,肥肉也一点都不腻,烤得略微焦香,包在芭蕉叶里又融入了一些清新味道。不了解是否是有提前腌制过,不用额外蘸辣椒粉也特别美味。那些天我们每天都在雨林里徒步,尤其容易饿,村里阿姨做的一大包烤肉很快就被瓜分完了。一只野猪我们大概吃了两三餐,之后餐盘里就好几天都没有肉食了,干巴巴又带酸味的Tempe(当地一种大豆发酵食品)是唯一的蛋白质来源。我才猛然意识到,在没有大规模工业化养殖业、尚以采集狩猎及种植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当地社会,肉食是不常能见到的奢侈品。
在我去到的达雅克部落中,村民家里都不养猪,猪肉基本只来自捕猎的野猪。一年到头,适合捕猎的季节也就两三个月。狗狗是达雅克人狩猎时的好帮手。虽然我没有直接亲眼见到达雅克人狩猎的场景。但我曾看见一个当地村民开着小船,载着一群狗狗前去森林里猎野猪的场景,令我震惊不已。很难来想象体型娇小、乖巧温驯的当地土狗如此有战斗力,竟能在地形复杂的原始森林里齐心协力和凶猛的野猪对抗。
Sisig是我和先生Da最喜欢的菲律宾菜。Sisig用中文简单解释,就是铁板猪内脏。
第一次吃到Sisig是在马尼拉的金融中心Makati市,如上海新天地一般繁华的市中心。在优雅的餐厅卡座落座后,当地好友强烈推荐我们一定要尝尝这道被评为“地表最强猪肉料理”的菲律宾菜之光。不一会儿,服务生便端上了炙热的铁盘,盘里的油还在滋啦滋啦地响。满当当的猪杂碎上打了一颗生蛋,鲜嫩的生辣椒片,以及对半切开的金桔、柠檬点缀在旁边,色彩斑斓。服务生利索地挤上柠檬汁,拿大勺将蛋液和柠檬汁搅拌进猪杂里。我迫不及待地舀了一勺,送入口中。哇,味道太棒了!猪杂碎肥瘦相间,口感脆爽,表层的一点蛋液为其赋予了一点丝滑感,而金桔和柠檬汁则在咸辣中调和进了一种独特的清香。各种味道不仅融合得颇为和谐,而且口感层次很丰富,咸酸甜辣,恰到好处。
Sisig是在菲律宾受西班牙殖民时期,由西班牙风味餐猪肉凉拌菜转型而来的铁板料理,经历了数次革新优化。目前的Sisig一般以剁碎的猪头肉、猪肝、五花肉等为主料,加入洋葱、金桔汁,快炒后放在热铁板上,上桌前再打入一颗生蛋,色香味俱全。
离开菲律宾后,我好多年没见过Sisig。后来来到阿联酋生活,我惊喜地发现广大的菲律宾移工社群也带来了价廉物美的菲律宾美食。而在所有的菲律宾餐厅里,Sisig必定是招牌菜。由于是在国家,所以这里的Sisig只能做牛肉、鸡肉或海鲜版本,不过丰富的口感和味道不减。我和Da几乎每周都会光顾菲律宾餐厅,也将这道菲律宾美食推荐给了身边的中国朋友。有个刚来这边工作不久的朋友J,第一次吃到Sisig就着了迷。之后一个月,他每天都点一份Sisig加一份米饭。
前两天写了可口的菲律宾美食,但这只是我带着游客的玫瑰色滤镜看到的菲律宾一角。我个人很惭愧的一点是,在马尼拉逗留的短暂日子里,我过得很离地,尚未有勇气真正走进菲律宾底层人民的生活。
去菲律宾旅游前,当地华人朋友A强调了无数次当地治安的问题,并千叮咛万嘱咐交待我过海关时候要硬气点拒绝官员的索贿。在马尼拉的几天内,我住的是需安检才能进入的五星级酒店,出行全程有当地朋友接送,我的双脚就没有在街道上行走过。
A是当地风生水起的企业家,经营着数十家知名连锁餐饮,连连登上各大商业杂志报刊封面。他祖籍闽南,出身贫苦,父母早年迫于生计下南洋打工。无奈父亲意外早逝,他是个遗腹子,上头还有两个姐姐。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漂泊在异乡,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年幼的他做过无数工作,在菜场卖果汁,在工厂折铁衣架,折不够量的话还会被妈妈拿铁丝条抽手。母亲虽然很严厉,但很看重儿子的教育,借钱也要供他读书。他也很争气,从菲律宾最高学府毕业后,他在中国叔叔和两位姐姐的帮扶下创业,并一步步建立了现今颇为知名的餐饮商业集团。
马尼拉分布着很多贫民区。街道是破碎的,开车难免经过一些破败的街区,脏乱不堪,污水横流。街边的铁皮屋是用东拼西凑的废料搭起来的,仿佛风一吹就会散架。经过这样的街区时,车子总会在歪歪扭扭的道路上混成一团,只能听天由命,龟速前行。不时会有衣衫褴褛的瘦弱小孩来敲打车窗,一双双大眼睛直勾勾地往里看,或者拿着一块肮脏的抹布热情地帮忙擦车窗。
这种时候,A总是冷冷地直视前方,叮嘱后座的我们绝对不能开窗,也不要去看那些小孩,恨不得一脚油门冲出去飞速逃离。我不知道现在每天都西装革履的A,他的童年具体是什么模样。或许,从底层爬出来的他始终害怕坠落,所以拼了命地在商业世界里厮杀奔跑,一刻也不停歇,更不容许任何恻隐之心让自己偏离成功的方向。也或许,人终究是会变的,记忆会遗忘,阶层之间的高墙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爬过高墙的零星几个幸运儿已到了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的另一位地陪M是土生土长的马尼拉人。身为跨国公司高管的她也是拥有三个儿子的超级辣妈,保养得年轻靓丽,Instagram上大部分内容都是健身和度假的精修照片。那天她身着热辣的紧身吊带短裙,一同现身的三个帅儿子由随行的保姆照顾着,像是她的另一套时尚单品。在她开车带我们去参观西班牙王城的中途,等红绿灯时,也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来敲打车窗。不远处,还有几个像小混混一样的青少年盯着我们这边看,似乎是一起的。
M面不改色,从容地直视前方。这个红灯有点久。不一会儿,她非常娴熟地用秀美的手指夹起挡杆旁的一块巧克力,放下一点点车窗,将巧克力从上面的缝隙中递了出去,然后快速闭上了车窗。我看到巧克力的形状已经融化到完全变形了。车窗外的小孩一把夺过巧克力,站在拥挤的车流中撕开包装,狼吞虎咽地舔舐起来。绿灯亮了,M淡然地踩了油门,车子快速开走了。车子里一片祥和,优雅的爵士乐轻轻地在淡香味的清凉空气里回转,除了牙牙学语的三公子嘟囔着地问了抱着她的保姆一句什么之外,谁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朋友的别墅坐落在迪拜安静的市郊,据这位朋友说左邻右舍都是阿联酋的达官显贵。对富人世界一无所知的我并看不出门道,只摩拳擦掌等待尝试家庭手作的印度料理。
餐前饮料是Lassi(一种酸奶饮品),冰冰凉凉的,是印度传统消暑良品,也利于肠胃消化。入口有淡淡的咸味,随后浓郁的复合香料味在口中散开,沁人心脾。喝的时候需要不时摇一摇玻璃杯,让杯底的香料均匀地融回酸奶里头,再大口大口喝下。
喝完饮料后,家佣上了两种餐前点心,有Masala Samosa(印度咖喱饺)和Momo(源自尼泊尔的蒸饺)。Samosa是三角形的,炸得黄澄澄的面皮里包裹着满满的土豆Masala,圆鼓鼓的,像小朋友圆圆的小肚皮。蘸一点酱料后,轻轻一咬,酥脆的面皮和着热乎的内陷儿一起落入嘴里,鲜香四溢。Momo和国内的薄皮小笼包几乎长得一模一样,面皮蒸得晶莹剔透,看得见里头红红绿绿的蔬菜肉馅。蘸一点辣椒酱吃,一口一个,也很是美味。还记得我第一次在印度街头看到Momo时,亲切得想掉眼泪。
正餐摆了满满一桌,融合了来自印度不一样的地区和印尼的风味。朋友的老父亲介绍说,“我们印度菜的一个特点是基本都是热食”。我不禁意识到,这可能是印度菜和中餐的一个共同点吧。
两道主菜是印式中菜:满洲鸡和四川炒饭,估计是朋友为了接待我们这些中国客人而叮嘱厨师特意准备的。除了主菜之外,桌上还有两道南印度风味小吃,Idli(蒸米浆糕)和Dosa(米浆薄饼)。一颗颗圆扁扁的乳白色Idli拥挤而整齐地排列在白色瓷盘里,像一只只乖巧的小鸡仔。Idli口感软糯,有点像发糕,本身没什么味道,蘸鲜香微辣的Sambar汤最为合适。Sambar汤是一种稀薄的蔬菜汤汁,各种蔬菜与香料一起熬得软烂如泥,满盆金黄色里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绿色和红色,单喝也很够味。Dosa是朋友知道我爱吃后让厨师临时加的。有两种风味,Plain Dosa和Masala Dosa。Plain Dosa薄脆,口感酥酥的,蘸酱料吃很香。Masala Dosa则是在里头加入了土豆Masala馅料,口感更丰富,外酥里嫩。
饭后,佣人端上现煮的Masala Chai(印度拉茶)。Chai是在厨房里煮好后,装在精致的镶金边白瓷茶壶里端出来的。然后,佣人俯下身将热腾腾的Chai一一倒到茶杯里,再奉到主人和客人手中。每一只茶杯底下还都配了托盘,颇有英式女王下午茶的高级感。这和我之前对Chai接地气的感知截然不同。相较于街头小店里的Chai,这个Chai的口味偏淡一些,奶味和香料味都没有很浓,不过整体非常顺滑爽口,饭后喝不会感觉腻,比较没有负担。
在印度朋友家的用餐体验对我来说四平八稳,没有特别惊艳。不过,我很喜欢相对清爽的家庭印度餐风味,比在餐厅里用餐后的感觉更轻盈舒适。而且所有餐食包括酱料都是家里厨师自制的,健康且卫生。朋友的父亲看出我很爱吃绿椒酱,便特地让后厨给我打包了一小份带回家,刚做的,保质期约莫一周。这种绿色的辣椒酱辣度适中,可能是加了什么香料一起研磨的缘故,辣味被整体清爽顺滑的口感衬得恰到好处,搭配各种烤饼吃都很合适。对吃货来说,投其所好的喂食真是最好的礼物了,我高兴得合不拢嘴。
此次拜访,我最不习惯的是处处有佣人服侍。虽然我在印度工作的时候身边几乎每一位中产阶级朋友家里都有全职或兼职的佣人,但是在阿联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家里有好多个全职家佣的情况。主人和家佣同为来自南亚的移民,彼此之间却有着泾渭分明的等级阶序。整个用餐期间,主人一家都只需在沙发或餐桌上端坐着享受服务即可。一位瘦瘦高高、身着运动装、脚踩拖鞋的南亚佣人小哥全程服务大家,端碗、上菜、舀饭、沏茶……厨师也是一位南亚小哥,体型略圆润一些,偶尔也会出来上菜。有好几次我不自觉地想自己来,或者随手帮忙传个碗盘之类的,都被身着宝蓝色雍容华贵纱丽的朋友母亲以温柔而坚定的手势制止了。佣人小哥跟我对了一下眼神,继续低下头乖巧地忙碌着。我内心五味杂陈,不知道怎么面对眼前这么直白而坚固的阶层差异。
那天晚餐和家人在外聚餐。酒足饭饱后,大家懒懒地瘫坐着。我扫视着桌上的残羹冷炙,盘算着要将哪几个打包回家。不经意间一抬头,我的眼神触到玻璃门外一位南亚面孔的中年男性。他皮肤黝黑,头发卷曲,应该有些时日没剪了,有好多撮张牙舞爪地四处乱窜。他身形有些伛偻,上身套着一件旧旧的蓝底花衬衫,扣子整整齐齐的。他对我羞涩地笑笑,露出的前排牙齿有一两颗缺失。对上眼神后,他跟我挥舞了一下双手,然后右手五指伸直合并在一起做成勺状,左手托着下巴,咧着嘴,做了三下往嘴里送饭的动作。随后,他的双手扯开上衣的第三颗纽扣,露出一小块胸口的肌肤,脸上的表情变得苦涩而扭曲。
我有点错愕,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在阿联酋见到饥饿的模样。在这个号称富得流油的海湾国家,乞讨是违法的。换言之,贫穷是不被允许的。似乎这一个国家的每一颗沙,都应该佯装成金子,为富贵皇权和国家资本主义唱赞歌。初来乍到时,整洁的街道、稳定的治安、肥嘟嘟的野猫曾使我天真地想象,会有一个国家可以靠石油资本和严刑峻法根除贫困和暴力。一百多万本国国民得到财政供养。八百多万移民需有工作或资本,并恪守本地法律,才能在这里获得生存的合法性。不止乞讨,偷盗、斗殴、甚至闯红灯都会被严刑峻罚,严重者会被驱逐出境。这是这个和谐社会的治理基础。但几个月后,我慢慢意识到,不被允许的贫穷和饥饿,在这一个国家依然存在着。只是这些痛苦只能在黑暗隐秘的角落,小心翼翼地苟延残喘着。而一个以土豪著称的国家为何如此害怕贫穷,以至于要将其狠狠打压,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了。
在此之前,我也曾听到过一位在咖啡厅工作的非裔朋友L在这里遭受饥饿的故事。L来自津巴布韦,活泼外向,英文沟通能力很强,因此很快就和咖啡厅常客我成为了朋友。大约一年前,她在一位朋友建议下只身来到阿联酋寻找工作机会,因为津巴布韦的工资太低了。她的机票和签证费是哥哥赞助的。终于抵达后,她却发现在异国他乡找工作困难重重。在得到第一个工作机会前,她努力了整整五个月。找工作的最近一段时间里,她好多天是挨着饿度过的,常常两天只能吃一顿饭。高昂的房租和续签费已经花掉了她所有的钱,哪有钱吃饭、坐车、上网呢?买机票回家更是天方夜谭。举目无亲,前途未卜,进退两难。她说她当时手足无措,整天以泪洗面。我没办法想象连饭都吃不上是多么绝望的境况,毕竟在这里花两块钱也是能买到一个饼的。我更难想象L是怎么挺过那段绝望的时间的。移工都是勇敢的人。这种勇敢,大多也是被绝境逼出来的吧。
但是我很羞愧,今天在亲眼目睹饥饿的时候,我却自私地选择了冷漠。短暂错愕后,我下意识地选择了躲避。我朝这位南亚男性挥挥手,尴尬地说了一声Sorry,就避开了眼神。我再次扫视了桌上的残羹剩饭,有一块完整的烤鱼和半碗没有人动过的米饭。我小声跟家人寻求建议,“要不我把这些打包给他?”家人摆出一副保护我的样子,义正言辞地示意我出门在外不要节外生枝。我偷偷地再次抬眼往门外瞄,搜寻那位男人的身影。他想必是非常饿了,他想要的也只是我们的剩饭啊。这时,一位穿着运动服的白人男性吃完饭走出餐厅,塞给了这位南亚男性一张纸钞。南亚男性连连点头哈腰道谢,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 上一篇: 模块化自动化技术 助力食品包装行业更环保 更经济 更高效
- 下一篇: 水果盘儿童画